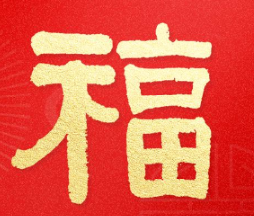福 · 伊秉绶 | 充实宽博、气势雄浑
一、隶书的中兴
前面叙述过隶书水平线条与竹简、木简材质的关系,抵抗竹简垂直纤维的毛笔会加重横向线条的用笔,最终形成隶书里漂亮的“波磔”。
三国魏晋是竹简书写过渡为纸帛书写的重要年代,纸帛开始成为汉字书写的新载体,成为汉字书写全新的主流。
毛笔在纸帛一类纤细材质上的书写,增加了汉字线条“行走”、“流动”、“速度”的表现,汉字在以“纸”“帛”书写的晋代文人手中流动飞扬婉转,或“行”或“草”,潇洒飘逸,创造了汉字崭新的行草美学,并取代了隶书成为主流。
故汉代以降,隶书的日常实用功能逐渐被楷、行、草书代替。入唐以后,隶书更被视为古体字,宋、元、明少有问津者;即便书家偶有涉猎,也多受时风影响,或唐隶带楷意,或明隶书中融入行草,结体、章法多出己意,法度湮灭,古意尽失。
清代乾隆、嘉庆期间及以后,随着古代吉金碑版的大量出土,考据之风、金石学、碑碣学盛行,篆、隶两种书体随之升温,热度回升,出现了一批篆书、隶书书法大家,将篆、隶两种书体的发展推向了新的阶段,清代也成为魏晋以来篆书、隶书发展的鼎盛期,后世称为“隶书中兴”。清代隶书直追汉代,但在创新在审美观上有很大的变化,个性方面更加突出,取法魏晋铭碑、唐碑,并在此基础上向汉碑字体回归,在继承汉代隶书后又赋予新的精神,清一代卓有成就擅长隶书的名家的人数也是汉以后历代所不可比拟的,如郑簠、金农、邓石如、伊秉绶、陈鸿寿、何绍基等都以专长隶书而著名,而且各有自己的个性和面貌。其他如郭宗昌、傅山、王时敏、万经、巴祖慰、姚元之、陈豫钟、张廷济、俞樾、翁同和、杨岘等,其隶书也很可观,形成汉以后的一代高峰。
二、八分
隶书书体,也称“分隶”“分书”。其名始于魏晋。清刘熙载《艺概》卷五《书概》:“未有正书以前,’八分‘但名为隶;既有正书以后,隶不得不名’八分‘。名’八分‘者,以别于今隶也。”
后世对’八分‘的解释纷纭不一,关于八分和隶书的异同也有很多解释。
三、伊秉绶(1754-1815)
字祖似,号墨卿,晚号默庵,清代书法家,福建汀州府宁化县人,故人又称”伊汀州”,宁化县城“福宁桥”牌楼中的“福”即取自伊秉绶的五字联。
伊秉绶喜绘画、治印,亦有诗集传世;工书,尤精篆隶,精秀古媚,用笔圆浑,不太强调笔画的波磔,横平竖直,结体方整,间架博大。行笔用墨多“飞白”,线条苍劲有力。
伊秉绶隶书为汉碑中雄伟古朴的一类,伊秉绶写隶书有着愈大愈壮,气势恢宏的特点,笔画平直,分布均匀,四边充实,方严整饬。因受衡方碑影响,以篆笔做隶,墨沉笔实,醇古壮伟,为清代碑学中的隶书中兴的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乾嘉八隶之首,他的隶书与擅长篆书的邓石如,并称南伊北邓。隶书尤放纵飘逸,自成高古博大气象,与邓石如并称大家。
曾出版于《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一)及《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等书。
1.各家评点
《清史列传》谓:“秉绶工八分隶。”
《国朝先正事略》谓其“隶书愈大愈见其佳,有高古博大气象。”与邓石如并称“南伊北邓”,又与桂馥齐名。以其“隶书超绝古格,在清季书坛放一异彩”而被后人瞩目,评价甚高。
清《昭代尺牍小传》谓“墨卿书似李西涯,尤精古隶,独不喜赵文敏,盖不以其书也。”
焦循《雕菰楼集》谓“公之起居言笑,蔼然君子儒也。时濡墨作隶书,如汉魏人旧迹。”
赵光《退庵随笔》谓:“伊墨卿、桂未谷出,始遥接汉隶真传。墨卿能脱汉隶而大之,愈大愈壮。”
蒋宝龄《墨林今话》谓:“(伊秉绶)尤以篆隶名当代,秀劲古媚,独创一家,楷书亦入颜平原之室。”
何绍基《东洲草堂诗抄》赞伊秉绶:“丈人八分出二篆,使墨如漆楮如简。行草亦无唐后法,悬崖溜雨弛荒藓。不将俗书薄文清,觑破天真关道眼。”
包世臣《艺舟双楫》谓:“余初识宁化伊墨卿太守秉绶于袁浦。墨卿,刘诸城之弟子也。因曾问诸城法,太守曰:‘吾师授法曰:指不死则画不活。其法置管于大指、食指之尖,略以爪佐管外,使大指与食指作圆圈,即古龙精之法也。其以大指斜对食指者,则形成凤眼,其法不能死指,非真传也。”
王椒畦诗曰:“墨卿作书亦如画,笔墨之外能通神。”
杨守敬《学书迩言》谓:“墨卿八分书根柢汉人,行书学李西涯,尤为超妙。”
向燊说:“墨卿楷书法《程哲碑》,行书法李西涯,隶书则直入汉人之室。即邓完白亦逊其醇古,他更无论矣。”
李宣龚云:“汀洲书法出入秦汉,微时所作篆隶有独到之处。即其行楷,虽发源于山阴、平原,而兼收博取,自抒新意,金石之气,亦复盎然纸上。”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谓:“汀洲精于八分,以其八分为真书,师仿《吊比干文》,瘦劲独绝。”
近人马宗霍《霋岳楼笔谈》谓:“世皆称伊汀洲之隶,以其古拙也。然拙诚有之,古则未能。独其以隶笔作行书,遂入鲁公之室。”
沙孟海说:“伊秉绶是隶书正宗,康有为说他集分书之大成,很对。其实,他的作品无体不佳,落笔就和别人分出仙凡的境界。”
2.隶书特点
追求古朴,追求“碑”味,以古人的思想改造时世,通过线条长短的变化,采用参差错落的并行方式,从而为书法注人了新的活力,达到了一种理性与自然的交融,完成了传承上的新的继承,实现了他创新的愿望。
主要取法于汉碑,如《衡方》《张迁》《孔庙》等的造型、气势;并揉进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李东阳的贴学笔意、韵味,形成了气势恢宏而又平和含蓄,雄强稳健而又柔和自然,威武庄严而又温和敦朴,开阔舒畅而又严谨端庄,内气鼓荡而又平静自如,苍茫浑厚而又滋润古雅的“中和”之美。
(1)方正、奇肆、姿纵、齐整与参差结合,平滑与迟涩裕配,最终构成了充实宽博、气势雄浑的艺术格调,具有苍茫劲健的古穆气息,大气磅礴,气势恢宏。
(2)字内架构与字外空间精心策划,长短参差的并行线条,增强了字内空间的可读性与趣味性。大小错落的外部空间所体现的变化,弥补了单一线条的时间节律。
与传统汉隶有很大的差异:他大胆地省去了横画的一波三折和蚕头雁尾,代之以粗细变化、甚至几乎没有变化的直线。于是,他以建筑般的结构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3)洞悉艺术朴素真挚的本质,但又深受儒家审美的影响。笔力扛鼎、雄浑磅礴,又气韵收敛、文气十足。
表现的只有一种气魄—种静穆的气魄,犹如一尊尊巨型雕塑聂立在我们的面前,使人产生仰视的感觉,而对此肃然起敬![]()